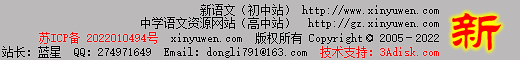| 梦也何曾到江南 | |
|
寞儿
梦也何曾到江南 2001年初冬,我独个去远方,去和一个陌生的自己约会。我去了周庄。 1989年一个春雨纷飞的日子,三毛在周庄哭了三次。我也是要哭的,是被一种魂牵梦萦的景致突然出现眼际,突然冲击心灵,突然撼动灵魂,又无话可说无话能说的哭,一种失语的哭,一种清泪洗尘的哭,一种游离现实成仙得道入诗入画的哭。 白水绕古镇,斜雨织静村。再加上那九百岁的风景:小桥、流水、人家、弱柳、摇船、水阁、骑楼、深宅、廊坊,还有发亮的石板路…… 这就是江南第一水乡──周庄。 一、似曾相识燕归来 走进周庄,我是走进了前世。 撞击我的,是要把我眼帘撑破的水乡格调。比如小桥上的一块石板,小巷路上嵌的一片碎石,船娘身上蓝底白花的工作服,船橹发出的轻矣声,挑晒在水巷上空的几件寻常衣物…… 对一个任性的寻梦人,周庄总会让人拾个心满意足。比如我在文化街购天蓝精镶米黄边短袖配喇叭裙一套,在西湾街买深蓝缀白花蜡染对襟中袖衫和双开叉长裙一套,在南市街再买白底碎蓝花和蓝底大白花旗袍各一件(咦,有花木兰东市买马西市配鞍的味道)。 我把梦装满了一袋子,很是高兴。这些我眼里最漂亮的服饰,只要能呆在衣橱里,就让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我的前世。她们被我前世的肉体遗落了,但她们穿在了我的魂里,从前世到今生;穿在了我的梦里,从女孩到女人。 哦,回来了,我的魂。 周庄有沈厅和张厅很值一走。在深深庭院悄然走过,竟有一种怕惊醒某个生灵的小心。所有在这里享受过富贵荣华的老爷少爷、太太小姐、伙夫厨娘,都上哪啦? 在沈厅,坐在内眷们习书教子的静室内,寂空空的感觉由心底而来,难道我会是这里生养过几个俏儿俊女的太太?没有谁能回答我,只有上帝知道这个秘密,只有四方小天井里穿向天空的丛丛修竹在叶落叶生中守着这个秘密。 张厅依然是江南大户人家的韵典,“人在厅中坐,船从家中过”的风情。奇怪的是我在这里找到的感觉竟是推磨,一推一拉间,我疑心自己是个粗婢。即便是又如何?做个周庄的粗婢,那也得是几百年修来的福气? 二、画廊里的女孩和篾屋中的老人 西湾街32号,有个女孩开了“晓雪画廊”。和别的画廊不同的是,这里的商品都是她的作品。我去时,晓雪不在,写生去了。在的是她有些拙朴的姐夫。他告诉我晓雪毕业于南京美术学院,九九年,晓雪只身从扬州来到周庄,慢慢地就有了自己的一片小天地。就有了中央电视台无意中的慧眼识珠,以及由此而来的专题片《晓雪画廊》。边聊,边很仔细地看VCD。晓雪长得不很漂亮,但皮肤细腻,秀发披肩,温温雅雅,有着江南女子独有的灵韵。细细软软地,她在片中叙述着自己在周庄的生活和感受,女孩颜晓雪,画家颜晓雪,我记住了她。 蚬江街27号,一个老人在做篾艺。86岁的沈发忠做了70年篾艺。如果把门面租给外乡人,一年轻松坐收一、两万。但他说:不想赚钱,坚决不租。他说自己要做生意。他的生意是邦乡邻们修补遗缺,一块竹扁,一把竹刷,一叠竹笼,能有几个进项?沈老说我不为钱,我为人民。他还说,太平桥下有一户,租个门面给外乡人,一年16万呀,现在的人,都被钱黑了心呀。 他摇头,我点头。心里想,这个老人有故事,看他的牙都要落光了。果然有。 文革期间和老太婆搞僵了关系,两人分吃分住维持到了今天。老人说,我就是不离。问详情,老人摇头,别提了,不想提。多少酸甜苦辣被我冒昧地问上心头。在每天的制篾手艺里,他织进了多少孤单、落寞和对现世的失望?他的门边,外乡人来了又走了,河里的水清了又浊了,一年又一年过去了,他的手艺泽福了多少乡邻的平常日子?又给他带来了多少比钱更多的自尊和成就? 他守着这门手艺,就如同守着那门坟墓里的婚姻。他的手艺顽固地生存在商浪滚滚的古镇。一生就那么几十年,用几十年来坚守一份希望或失望是否明智?而沈为忠他愿意,他愿意用他的守来证明自己的活。 三、最后的守望者 水乡的夜晚谁是最后的守望者? 周庄的夜是比白天更能自主自在的。周庄的白天人太多,多得有些像在清纯少女身上涂脂抹粉。粉黛不是她的性情。入了夜,游人退去,洗尽铅华,周庄终于可以喘口气了。 于是,红灯绿灯亮起来,三三两两,疏朗淡泊。光落进水里,陪水波轻舞;月亮升起来,悄无声息。柔柔地,给古镇的白墙黑瓦,石板巷路,大桥小桥,扶杨弱柳,披上轻纱。静下来,一切都静了下去,静得走在镇上恨不能与月亮对聊。寒意微微沁入体内,夜风里看灯笼轻摇,看招幌悄摆,只以为自己也溶入了静谧。一只黑猫安静地走过桥面,在你静坐的膝下绕来绕去,你晃惚间就以为自己变成了一只周庄的猫。 一天晚上走在古镇的青石街上,远远地就听见悠悠的《二泉映月》清澈地飞穿在古镇的夜空,有要划破水乡静宁的意思。却没有。相反,水夜因了琴声的相伴愈发宁静了。循着琴声,我不由放缓步子,走至太平桥,一个粗脸汉子正坐在桥头听琴。琴声却是从桥畔的骑楼传出的。 我在粗脸汉子的另一侧坐下。听琴。看灯在河床上跳舞。看月亮在天空爬上桥顶。再后来,汉子走了,桥上空余一个女人,忘了所有,不知心神何往,只恨不能化了河里的一道水痕,空中的一阵轻风,柳梢的一抹冬绿,永远投生在周庄…… 突地,响起一声“好”,喝酒的赏了拉琴的50块钱。“好”声里粗脸汉子坐回桥头,“好”声里琴师眉开眼笑下楼,哈着腰给了汉子应有的抽成,又颠颠地乐回了家…… 有女声从楼上飘下:你们都听出了些什么呀,我怎地一点感觉没有哇?有男的说,你的心怎地这样粗糙呀?女的就叹了一口气,也许是这几年在日本给弄的…… 我总算坠入了地面。 耳里的二胡没了,心里的失落却来了。 我也叹了一口气,多亏有了在桥头不掏钱而倾神赏琴的外乡女子,2001、11、25夜,周庄古镇的二胡声才填充上了别样的意义。 好景常遇,赏好景的人却不能常求。 曾听到两个游客对话。甲问乙,游完了?乙答,游完了。甲又问,总体印象?乙说,这里到处是猪肘子。(注:万三猪蹄,周庄主要名产。) 难怪乎三毛在写给周庄作家张寄寒的信中要说:“我们要把周庄当一个文化的珍宝,只有有资格的人才可以去,那些三姑六婆,省了罢。” 四、孵三毛茶楼 孵三毛茶楼,是周庄之行的压轴戏。 太阳透过红木古格窗,暖暖地照在古旧的八仙桌上。鸟声啾啾。评弹游丝般地若有似无。檐角下挑出的“三毛茶楼”招幌在轻风中荡着,白底蓝边蓝字总觉得不尽合乎三毛的味道。 喜欢三毛是没有理由的。爱到不仅喜欢她的生,也喜欢她的死。这是我和多数三毛迷们不同的地方。许多年前写下“三毛,生耶?死耶?”时,我没想到会在三毛悄然来过的周庄,在到处有着三毛音容笑貌的简陋茶楼里,努力地试着再次进入三毛的世界。 三毛用自主结束生命的方式来实现此生的终极救赎,那么来世呢?希望来世的三毛不要生就一颗敏感不安的心。哪怕蒙昧一点,快活而平常地活过一世该有多好? 而我的来世愿作一只鸟,自由自在地飞过。什么也不要留下,什么也不可能留下。 一切都是命定的,三毛注定要成为大家的三毛,却依然可以不管不顾活出自己;我注定是个平庸的女人却畏畏缩缩活不出自己,没有谁可以改变。正如那刻我在茶楼里,在三毛的注视下随意地写着手记,而没有一个游人上来打扰,那幅场景不会是几百年前就安排好了的吧? 三毛没有跌入过周庄的夜,她只在周庄的白天走过。她说过要来周庄再小住几日。可惜,她带着梦走远了。在这点上,我比她幸运,我沉入了周庄的水底。拥有过周庄的朗月和清夜。 在周庄,你一个人安静地哭过,哭的意义只有你独个知道。你哭的时候,隔壁又一对男女在疯狂地造爱。他们对周庄毫无敬爱,肆无忌惮。来周庄的一拔又一拔人中,这类人大有人在。你以为他们是在强奸水乡,但你不能去指责人家。周庄,只是你个人世界里的少女,清纯质朴,你爱她又疼她。在那里,你大声说话都不敢,你总是细细絮絮地,不知不觉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水样的女人。如果一定要爱,那也该是一场不出声,静静悄悄的爱。 周庄不能容忍疯狂。 周庄是我灵魂秘境里的一件蓝底碎花旗袍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