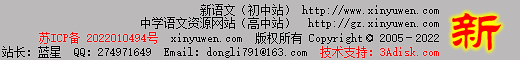姐和弟
在我们姐弟六人中,大弟排行老二,是爸妈托人保的子。在我模糊的记忆里,家人为此事还还了愿,具体的程序我已经记不太清了,就知道一切都是按照算卦先生的安排。长大后我知道那不过是骗人的把戏,根本没有科学的根据。可在民间却行得通,我的父辈们都相信至极。
爸爸是转业军人,妈妈结婚前就是女干部,我认为就凭他们的觉悟也该不信那一套,可他们却不折不扣地遵照了,我想可能是因为大弟的缘故吧。因为在我上下各有一个男孩都未成活,这就象人一旦生病就会乱投医一样,心情使然。这次能如愿,更让他们不得不相信了。
大弟问世后,望子成龙心切的爸妈,给弟弟取名苏州,他们希望儿子功成名就,起码将来能当个一官半职的,这样就能光宗耀祖。可弟弟后来却偏偏经了商。
大弟小时侯,可算是历经磨难。
出疹子时高烧不退,他整整昏迷了近一个星期,妈妈也就在床上抱了他一个星期,总算闯过了坎儿。
三、四岁时,他又得了“羊毛疹”,当时给他挑“羊毛疹”的场面如今还经常在我眼前浮现:针尖像是挑到钢丝上一样咯嘣——咯嘣——地响着,弟弟撕心裂肝似的嚎叫着,爸妈束手无策地流着泪,我担惊受怕地躲闪着、偷看着……
一天夜里,大约二、三点钟,爸爸突然把我喊醒,说是让我起来闩门,他和妈要带弟弟到集上看病,我迷迷糊糊地爬起来,按照爸的吩咐闩好门后,在昏暗的灯光下,我脑子中一会儿出现了红眼红鼻子,一会儿又想到了大灰狼……吓得我不敢吹灯,,躺在被窝里也不敢睁眼。后来爸爸回来拿东西,说是弟弟住了院。满头大汗的我才开了门,这时,我发现太阳都升到一树稍高了。爸爸告诉我,弟弟得了脑膜炎,医生说,幸亏来得及时。
弟弟小我六岁,他是在我背上长大的。我上小学时,他刚刚学会走路,农忙时家里没人领,我就带他上学,经常是我上学时,爸爸把他送到学校,等放学时爸爸或妈妈再把他接回来。有时爸妈都不来,我就背着他往家挪,同学也经常帮助我背弟弟,我打心眼里感激。
记得我刚开始领弟弟时,经常好和翠兰在一起,她也是领弟弟。那时,七岁的我身材矮小,怎么也背不动弟弟,我就哄着他玩,不一会儿,腻烦了的弟弟就自己顺地爬,我拦也拦不住,我看到他磨红了的膝盖时,就用小手摸着伤心地哭,比我大两岁的翠兰这时就会帮助我。我那时很感激翠兰,我们全家都感激她。妈妈为了表达心意,农闲时给我和弟弟做鞋,总忘不了有她的份。今年清明节前,我回家给爸爸上坟时,遇到了翠兰,我们当时都没认出对方来,她把我说成是我小妹雪芳。我看了半天只是陪笑,不敢说话,后来经妈介绍,我们才认出对方来,这也难怪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没见过面了。那天,我和翠兰我们都紧握着对方的手,谈了很久,很久。我们提到往事时都倍感亲切,那一刻我们俩仿佛又回到了从前。
弟弟上学后,一直很努力,在学校多次竞赛获奖。第一次中考失败的他,随我和爱人到新兴重读。虽然那时我们工资不高,三个人吃饭还是过的去的。弟弟很懂事,也很听话。在新兴的一年中,我和爱人总是说一不二,弟弟从来都是听之认之。记得那时我和爱人刚结婚,出在磨合期的我们经常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,不知道影没影响弟弟的学习,就一件事我至今还耿耿于怀。在弟弟临近中考时,怀孕近四个月的我因拆洗被子而大出血,当时爱人不在学校,虽有同事帮忙,可也把弟弟给吓坏了,记得他有两顿都未吃饭。是年,弟弟中考再次落选,为此事我一直有愧于心。
弟弟中考差了几分,但那年他考上了亳县一中,可是当时的家境不允许他继续上下去,特别是上高中。比他少近二十分的董群上了亳县一中,后来他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,再后来又读了研究生,现在在上海工作。可是弟弟却带着遗憾退学了。
退学了的弟弟,先在家务农,后来经人介绍到凤台县砖瓦厂干了一段时间,接着又到涡阳肉厂扛了几年的包,再后来,他自己跑到合肥学修家电,中途改学修钟表。开始只是在街上摆个摊,全部家当就是一个桌子、一个凳子,还有一套维修工具。第一次他接到了一个手表,手哆嗦着不敢打开,惟恐拆开后装不上,后来在家人的鼓励下,他战胜了自我,那是他踏上商界关键的一步。接着他从摆摊到租房,再到自己购买门面房(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),就这样他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。
弟弟诚信有余,睿智不足。不知是天生还是小时侯脑炎使然,前者使他门庭若市,后者令他平生几多烦恼,同时也交了不少的学费。做生意的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,再者街上的人又个个猴一样的精,要想在街上打下一方江山谈何容易?!弟弟能尽快地成熟起来是我们全家最大的愿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