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实习记者周喆/上海报道
2005年8月7日,上海书城,余华新作《兄弟》的签售活动持续了近两个小时。结束签售后的余华看上去既疲惫又兴奋。他忽然笑着给记者展示了手里的一个石榴,那上面写着“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:你对小说里的两个时代怀有怎样的感情?
余华:这两个时代我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,感情都非常复杂。第一个时代显然是一个反人性的时代,但因为自己童年和少年都是从那里经历过来,就永远难忘,永远怀念它。第二个时代我们正在经历着,有很多很好的东西,但我称之为一个人性泛滥的时代,它有很多毛病。我生活在其间,还是要感谢它。对于人的一生来说,能够经历这么两个有着天壤之别的时代,是一种幸福。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:在后记中你用了三个词来形容当代:伦理颠覆、浮躁纵欲、众生万象。后面一个是中性词,前面两个似乎都是贬义词,其中是否表达了你的某种担心?
余华:我用这三个词并不是要贬低或者抬高这个社会,只是对小说下部的内容的概括。对这个国家用不着担忧,我越来越相信我们中国有着强大的免疫力,多少问题要是换在别的国家可能就完了,但是它没事,它一年又一年挺过来。我记得从90年代初起,有很多国外的所谓智囊人士都预测中国哪道坎会过不去,但我们都过来了。怎么过的,自己都不知道。中国的免疫力是全世界最强的。任何问题,它自己都能解决。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:中国历史从文革到今天,你如何理解其中的延续与变革?
余华:这个问题比较复杂,很难用几句简单的话来表达。这也就是我写这么长的一部小说的原因。出国后,我才知道西方人这半个世纪的生活没有多少变化,而我们这半个世纪的变化是天翻地覆的。所以我在后记中有一个比喻:文革和今天比较,相当于欧洲中世纪与欧洲现在比较。假如欧洲的中世纪是以文艺复兴为结束标志的话,到今天也有四五百年了。在西方一个人要活四五百年才能经历的变化,在中国,活到40岁以上的人就已经都经历了。这对我来说是弥足珍贵的。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:现在很多人有一种担忧,就是若干年以后,年轻一代的人可能会完全抛弃这种沉重的历史感。
余华:我觉得他们很难抛弃沉重。他们虽然可以抛弃文革的沉重,但现在他们已经面临着一种新的沉重。这个时代的沉重,是一种没有方向的,方向混乱的沉重,不给你指定任何方向,你自己爱往哪儿走就往哪儿走。而文革的沉重在于你没有方向,必须沿着指定的那个路走。所以两个时代的沉重是不一样的,而且同样令人感到不安。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:现在不少作家的写作都避开现实,而你却坚守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,并在这部作品中更突出了历史和现实感,这是为什么?
余华:我一直在关注中国的现实。用现实的方式写小说,并不是就不需要想像。它也需要,而且对想像力的要求更高,因为它要求有一个把握。如果把时代特征虚化地去写是很容易的,而鲜明地去写当然就会增加很多难度,我想我有办法克服它。我希望在下一部作品里可以把今天这个时代表现得更加充分一些。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:有人说你的小说对“小人物”怀有悲悯之心,对此你怎么看?
余华:我自己也是小人物。起码我的成长过程都是一种小人物的生活体验,你让我写大人物,我真写不了,我最多写到一个处长。莫言有一个非常好的概念,他说作家不是“为”老百姓写作,而是“作为”老百姓写作。因为多一个你、少一个你,人民日子也没有变化,人民不需要你去代表。但作家要作为人民的一份子来写作。我就是把自己作为小人物来写作的。
图书连载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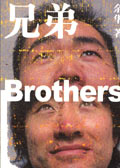
(编辑 小题)
|
|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