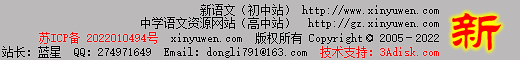老话讲“病来如山倒,病去如抽丝”,不仅抽丝,这场感冒还带走了我近八斤的体重,代价是留下两条自我感悟:一是到了这般年纪,身体外强中干,不打针光靠吃药,说什么再也无法生扛过去了;二是自己的精力真的有限,已经无力分身来应付这样级别的折腾!
病就像是接力棒,古代就有大病将愈时把病转嫁给偶遇的倒霉蛋一说,想来我就着了这个道。前几日,为了尽快完成工作,于是鬼迷心窍地给一好友兼作者打电话死命催稿,不巧对方发高烧正打点滴,简单的问候替代例行公事的寒暄之后,借着黄世仁的狠劲,于是说了如下一番回想起来令自己都心寒的话:“没事,稿子随便你瞎写,发高烧正好,反正也是胡说,写不好还写不坏吗?好赖不济,死活不管,记得明天交稿啊!”不知是病毒已经进化到可以借电波传染,还是朋友挂了电话后憋着一肚子悲愤和怨气暗自发功,总之我病了,病得不轻。
灾病无情,生计无义。有朋自远方来,我可以借病推掉叙旧言欢,但报社派发给我的活儿却说死也推不掉。一边是一个月的五斗米,一边是不断飙升的体温,左右权衡、穿裹严实、冒雪夜奔、决意上路——要死也得死在工作岗位上,这样还能评个烈士!
工作任务说起来很简单,就是天不亮要准点儿赶到城市的另一端去监察本报的发行工作。雪后的凌晨,空荡荡的街头只有我和妻子相互搀扶的臃肿身影,出租车、三轮车一辆都见不到,要不是借着发高烧取暖,我想自己用不了多久就得冻僵了!祸不单行,好不容易盼来了一辆出租车,但没出几里地车就坏在了前不着村、后不着店的立交桥上。没办法,我和妻子只有下来推车,那情形颇像雷锋夜送老大娘回家或是地下党抢运抗战物资……
捱过了忙碌的清晨,我的病更重了,体温史无前例地突破了40度大关。慌不择药,试遍家中的各种常备药,体温略有下调,但口腔内却出现了大面积溃疡,到医院医生看都不用看就得出结论:乱吃药过敏了,赶紧拍片子、验血、打针吧!
发高烧不能奈我何,但口腔溃疡却要了我的命:不能进食,也不能说话!不吃东西咱可以消耗以往积攒的脂肪,权当减肥,但不能说话这日子就没法过了。眼前的困难就是不能接电话,只好示意妻子代劳当传声筒,并急中生智,奋笔疾书写下三条应对答复:A、有事出去了,电话忘带了。B、正在洗澡,不便接电话,有事可以转告,过后给你回短信。C、口腔溃疡,据实相告。父母来电话就用A方案搪塞,朋友相邀就用B计划挡驾,单位来催稿就用C理由收买人心。
说实话,这一招并不灵,除了父母,似乎没有人相信一个中年人能手机离手。
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感冒,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无力应对。病魔和琐事像是商量好了似的结伴而来,越着急体温越高,这令我一度绝望,悲凉中似乎看见一个轻轻松松的自己向着另一个方向快活地走远,不知是出于嫉妒还是惊吓,睡梦中我竟然向着他大喊一声:“兄弟,走错了,这边!”
妻子说我这是高烧烧糊涂了,到点儿该打针吃药了。
作者:纳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