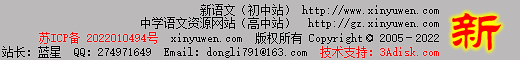怀念
黑夜里的那双手
我怀念那个夜晚。
如墨的夜色涂抹了一切,漆黑的背景里,远山隐约的轮廓比白昼显得矮小,但多了些森严,像长短不一的刀枪剑戟,紧张地举起来,刺向从陡峭处黑压压扑下来的天空。河流忽然收起了温柔的光波,发出恐吓的声音。这是我第一次走夜路。一段并不长的路,我走得比我的记忆还要漫长。我的小手里攥着一把石子,随时投出一粒,吓唬那些我想象中可能出现的鬼影。我的衣兜里揣着一本从小朋友家里借来的书,书里讲述一个善良孩子勇敢的故事,我断断续续回忆着书里的情节,为我颠簸的脚步壮胆。夜更黑了,远山的刀枪剑戟不见了,莫非被收缴?墓地的磷火却闪动起来,令我想起一些可怖的眼睛。我的心跳加快,咚咚咚,我清楚地听见了我身体里的鼓。我在一块大石头旁边停下来。我不敢再往前走了。我靠紧石头,想象它就是我的祖父。接着一片片冰凉的东西落下来,一摸,才知道是雪片。我就在这里过夜?我就这样让雪覆盖?我身体里的鼓敲得更响了。
这时,一个微弱的、温柔的声音传来:“我领你回家,不要害怕。”是母亲的声音,但不是我的母亲,是与我的母亲的声音同样微弱、温柔的声音。她拉起我,拍拍我的肩膀,说:“我是你同村的王婶。”王婶,不就是那个被斗争的地主婆吗?我在斗争会的外边曾看见过她被辱骂、被打的情形。五十多岁的脸上,织满了一百年以上的皱纹。她说她今天到水库筑堤坝加夜班刚刚回来,她喘息着,说话很吃力。她一手扛着铁锹,用另一只手握住我的手,我感到她的手那么粗糙,满手都是硬茧。此刻,我感到这双长满硬茧的手是这样温柔和温暖。
多年了,我仍然想,残酷的生存给她的是粗暴和凌辱,而她仍然以那双手传达爱意和温情。
当她把我送到家门口,她轻轻地从我的手中移开她的手。她说,谢谢你,是你的小手把我的手暖热了。我当时竟然无话可说,也许是被这浓黑的夜里突然出现的光亮照晕了,也许是并不理解这双一再被生活伤害的手所传达的爱的珍贵。今天,我有太多的话要对那双手表达,但那双手早已回到夜的深处。
少年的松林
我怀念那片松林。
我走进去,就看见了一丛丛蘑菇,露水停在上面,像谁忘记收回去的明亮的眼神。我简直不忍心采摘这些蘑菇,太美丽,太纯洁了,莫非这是松树开在地上的另一种花朵?这么好的花朵肯定有别的更高的目的,我怎么能摘取呢?我走进松林的时候,并没有得到松林的许可,是我自己闯进来的。这纯净、湿润、混合着腐殖土、野花、树木气息的空气,我已经无偿地大口大口呼吸了;这铺着松针和苔藓的柔软的地面,我已经踩踏了;这正直的树干、碧绿的针叶所呈现的伟岸和活力,我正在领略;溪水从草丛穿过,留几句叮咛又隐入林子深处;树枝间的鸟语,我听不懂一句,每一句都像是说给我的。松林啊,这么多这么多礼物,我都领取了,我都享用了,我还要采摘你开在地上的花朵吗?我凝望着那些天真纯洁的蘑菇,手,伸出又缩回,伸出又缩回。在美面前,我的手变得羞涩胆怯。在纯洁面前,我的心守住了纯洁。
我终于背着空背篓走出了松林。回头看,林子那么静,那么深,那么神秘,又那么空灵,它幽静的深处,藏着多少露水、花朵和鸟声,藏着林子外面很难找到的蓝色的梦境。我感到我的背篓并不是空的,盛着我一生中最纯洁的记忆。
多年以后,世上多少林子消失了,多少鸟儿匿迹了,但是再锋利的斧头,也无法砍伐我内心里的那片松林,它固守着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水土,在最荒凉的季节,我也能听见多年前的鸟鸣,看见湿润的地面上,那美丽的蘑菇,露水停在上面,像谁忘记收回去的明亮的眼神……
小 白
我怀念那条白狗。
是我父亲从山里带回来的。刚到我家,它才满月不久,见人就着走,过了几天它才有了内外之分,只跟家里人走,对外人、对邻居它也能友好相处,只是少了些亲昵。我发现狗有着天生的“伦理观”和“社交能力”。不久,它就和四周的人们处得很熟,连我也没有见过的大大小小的狗们也常在我家附近的田野上转悠,有时汪汪叫几声,它箭步跑出来,一溜烟儿就与它的伙伴们消失在绿树和油菜花金黄的海里。看得出来,是小小的狗的群落里一个活跃的角色。我那时在上高中,学校离家有十五里,因为没钱在学校就餐,只好每天跑步上学,放学后跑步回家吃饭,然后又跑步上学,只是偶尔在学校吃饭、住宿。我算了一下,几年高中跑步走过的路程,竟达一万多华里。这么长的路,都是那条白狗陪我走过来的。每一次它都走在我前面,遇到沟坎,它就先试着跳过去,然后又跳过来,蹭着我的腿,抬起头看我,示意我也可以从这里跳过。到了学校大门,它就停下来,它知道那是人念书的地方,它不能进去,它留恋地、委屈地目送我走进校园,然后走开,到学校附近的田野里,等到我放了,它就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口,亲热地蹭着我,陪我从原路走回家。
我一直想知道在我上课的这段时间里,它是怎样度过的,有一天我特意向老师请了一节课的病假,悄悄跑出校园观察狗的动静。我到食堂门口没有找到它,它不是贪吃的动物;我到垃圾堆里没有找到它,它是喜欢清洁的动物;我到公路下面的小河边找到它了,它卧在青草地上,静静地看着它水里的倒影出神。我叫了它一声“小弊“(因为它通体雪白),它好像从梦境中被惊醒过来,愣愣地望了我一会儿,突然站起来舔我的衣角,这时候我看见了它眼里的泪水。那一刻我也莫名其妙地流出了眼泪,我好像忽然明白了生命都可能面对的孤独处境,我也明白了平日压抑我的那种阴郁沉闷的气氛,不仅来自生活,也来自内心深处的孤独。作为人,我们尚有语言、理念、知识、书本等等叫做文化的东西来化解孤独升华孤独,而狗呢,它把全部的情感和信义都托付给人,除了用忠诚换回人对它的有限回报,它留给自己的全是孤独。而这孤独的狗仍然尽着最大的情义来帮助和安慰人。这时候狗站在我身边,河水映出了我和它的倒影。
后来我上大学了,小妹又上高中,仍然是小白陪着妹妹往返。妹妹上学的境遇比我好一些,平时在学校上课、食宿,星期六回家,星期日下午又返回学校。小白就在星期六到学校接回妹妹,星期日下午送妹妹上学,然后摸黑返回家。我在远方思念着故乡的小弊,想着它摸黑回家的情景,黑的夜里,它是一团白色的火苗。有一次我梦见小白走进了教室,躲在墙角看着黑板上的字,它也在学文化?醒来,我想象狗的脑筋里到底在想什么,它有没有了解人、包括了解人的文化的愿望?它把自己全部交给人,它对人寄予了怎样的期待?它仅仅满足于做一条狗吗?它哀愁的深邃目光里也透露出对人、对它自己命运的大困惑。它把我们兄妹送进学校,它一程程跑着周而复始的路,也许它猜想我们是在做什么重要的事情,我们识了许多字知道了一些道理,而它仍然在我们的文化之外,它当然不会嫉妒我们这点儿文化,但它会不会纳闷:文化,你们的文化好像并没有减少你们的忧愁。
后来小白死了,据说是误食了农药。父亲和妹妹将它的遗体埋进后山的一棵白皮松下面,它白色的灵魂会被这棵树吸收,越长越高的树会把它的身影送上天空。那一年我回家乡,特意到后山找到了那棵白皮松,树根下有微微隆起的土堆,这就是小白的坟了。我确信它的骨肉和灵魂已被树木吸收,看不见的年轮里寄存着它的困惑、情感和忠诚。我默默地向白皮松鞠躬,向在我的记忆中仍然奔跑着的小白鞠躬。
那条河流
我怀念那条河流。
远远地看,它就像一根孤独的琴弦绷在原野上,任风雨和岁月弹拨。
我是生长在它旁边的一双耳朵。当时我不觉得幸运,以为这音乐、这波涛的诉说、这不尽激情的灌注,都是理所当然。以为这柳阴是理所当然的,洋槐洁白芳香的花絮是理所当然的,竹林里布谷鸟黄鹂鸟的啼鸣是理所当然的,两岸湿润的炊烟和歌谣是理所当然。
当时幼稚的心里,却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念头:这河流以及与它有关的一切,理所当属于我们,就像我们与生俱来的血管、手纹和酒涡,它是我们理所当然的部分,它肯定能伴随我们始终,并永恒地绵延。
我在河湾里学会了游泳。我把蝴蝶的姿势、青蛙的姿势展示给水中的鱼;我仰躺在水床上,看天,在天蓝和水蓝之间,我漂浮的梦。我捉螃蟹,石缝里小小的反抗弄疼了我的手,而它没有多余的恶,小小的身体上全是武器,一生都在战争的恐惧里度过,最大的成功仅仅是防止过分的伤害。在横渡湾的时候,我遭遇过一条水蛇,小小的头着,更小的眼睛圆睁着打量陌生的天空,它也在不测的水里横渡它的命运。夏夜,透过薄雾,我看见母亲们被清水洗浴的身体,那么美丽洁净,浑圆的乳房冒着水汽,天上密集的星星都把目光投递过来,也认为这里就是天堂。
我在柳林里完成了对一个女孩子的第一次吻,有一种犯罪的感觉,但是很幸福,幸福得羞而眩晕。我在竹林里制作了第一管竹笛,摹仿北斗的指法(它也是七个音孔),我在静夜里向身后的村庄和远方的岁月吹奏;我在芦苇荡里射出了少年的迷惑和激情,一枝枝温柔的苇箭,射向天空又原路返回,命中内心里最初的秘密……
当时,我不觉得这一切都是奇迹,我不觉得我内心水域,有多一半是来自这河流的灌溉。
那浮浅、单纯、蒙昧的心里,以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。我没有想过这河流会有断流的时候,我没有想过它似乎源远流长的水,是来自哪里?它的温柔碧波和浩然激流,是怎样一点一滴汇成?
带着它的涛声和波光,我湿淋淋地走了。我走到哪里,就把它带到哪里,我是它站起来行走的一部分,我的记忆里流淌着它的乳汁。
我仍觉得它理所当然存在于那里,理所当然属于我,属于我们,而且永远。年前回家我愕然了。我再也看不到那条河流。横卧在面前的,是它干涸的遗体,横七竖八的石头无言诉说着沧桑;岸上的柳林、竹林、槐林、芦苇荡都已消失,荒滩上,有人在埋头挖坑淘金;三五个小孩,在放一只风筝,几双眼睛一齐向上,望着空荡荡的天空,和那只摇摇晃晃的风筝。
我已找不到当年游泳的地方,那让我感到深度、照过我少年倒影、用蓝色的漩涡激起我最初诗意想象地方,已被高大的垃圾堆覆盖。
抚摸过母亲们胴体的月光,忧愁地打量着荒凉的沙滩和龟裂的石头。
我多想拔出留在记忆里的那些苇箭,交给孩子们,让他们射向葱茏的夏天。
我多想,我多想找到死去的源头,去大哭一场,让泪水复活这条梦中河流。这时候,才痛彻心肺地明白:天地间没有理所当然永远属于我们的事物。
理所当然,理所当然地去珍惜---
这才是惟一属于我们的理所当然。
们不过也是游荡于河流中的另一种鱼。我们不愿成为干鱼,但我们很可能要把自己折腾成干鱼。许多河流枯竭了,污染了。爱,枯竭了;我们内心的河,不再是碧波倒影,而是注满了污水,堆满了垃圾。
我该怎样打开内心的纯洁水源,复活那死去的河流?
理所当然,我必须问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