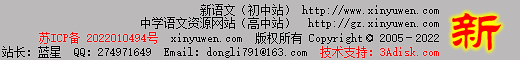回 答
王家新
“苦难尚未认识……” ——R·M·里尔克 “女权只是蓝图,那些勇敢的女人已经死了。” ——沈睿要回答一首诗,需要写出另一首,事情并不那么简单。勇敢的女人正在诞生,她就出现在这首诗里。她讲了一个(中国)女人的故事,她就在这种叙述中诞生:她来自和你一起共同生活的过去,但她又是新的。她光彩照人,让你刮目相看,她甚至迫使你接受挑战;为此你得报答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。回答一首诗竟需要动用整个一生,而你,一个从不那么勇敢的人,也必须在这种回答中经历你的死,你的再生。 为此你不得不再次回到过去,纵然一次次你从那里疲惫而归;十年,二十年……我们的国家,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朋友和亲人,发生了多大变化呵,虽然伟大的史诗尚未产生,你却仿佛已走过了远远超过一生的历程;我们的过去,我们的初恋,已变为一张张黑白照片,恍若隔世让人不敢相信。我们还属于从下放的山乡来到大学校园的那一代人吗?不,珞珈山已是墓园埋葬了我们的青春。 这些天我住在德国南部的一个古堡里,二百年前一位偶发奇想的公爵建造了它,作为日后幽居之所——但时间却它赠给了另外一些人的沉思。我出没于它的荒废花园;我震摄于笼罩它的森林的静寂;我登上它的巴洛可回廊:我是否看清了一个人从山下走过来的历程?我能否让一个审判的年代从这里再次升起?我自己的全部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?我又能否让我自己和我的同时代人一一从我的写作中走过,并脱下面具,为了向一种黑暗的命运致礼? 深秋的夜。我刚刚从弗兰达那里回来,这个美丽的,一直在凝视你的有着一头金色卷发的意大利女孩,建筑艺术家,在给我作了浓浓的意大利咖啡后坐下来,唱起了关于她家乡的歌—— 那不勒斯,你有一千种颜色 那不勒斯,你有点让人害怕 那不勒斯,你是孩子们的声音,他们 在渐渐长大 那不勒斯,你是海的味道,海的歌 那不勒斯,人人都爱你 没有人知道你的真实 于是我想到了你的诗,和我们的生活。是呵,什么是“真实”?我不知道。我只是看到我所爱的人们,只需要一种修辞就把历史创造了出来。谁能正视自己而不是把他留给另一个鲁迅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去审判?“真实”?让我放弃。我看到的真实早已消失在时代的滔滔宏论中,人人都在“真实”的名义下为那荒谬的一切而战。我不再辩白。我也几乎不再关心自己是谁,而只是想说:这就是我们的时代——你的痛苦,你的生活,你的真实只是这部伟大传奇中的一个细节。 那不勒斯的海远去了,弗兰达在期待着。她是如此美,不是漂亮而是美;同样,不是聪明,而是INTELLIGENT;我们用笨拙的英语交谈着,竟能深深地理解。她先是用拉丁文背诵了维吉尔,而后又谈到《神曲》的“结构”——因为我提到了但丁。弗兰达在期待着,我懂。我已把她写入诗中,接着我还会为她写诗——为了她那再次向我凝视的目光,也为了那一直在提升着但丁的贝亚特丽采……但,我的身体却在变沉。我竟从她那里回来了:你的信和诗在等着我。我知道我的过去总会在某个时刻向我发出符咒。我回来了。我从弗兰达的二楼回到我的顶楼,回到我的地狱。 我需要回答吗?我必须。这是一种什么力量,我们早已分开,我留在北京,清晨我醒在一片雨声中时,也许你正驱车在美国西北海岸的最后一道夕光里……但我们仍在一起。十七八年了,我们在一起,从大学同学到结婚,到有了孩子,到你渐渐变得我不再认识,到不成问题的一切都成了问题……也许有朝一日我会冒胆说出我生活的故事,我会让一本书来总结我们、回忆我们,但此刻,能否让我不再想到你让我达到一种智者的平静,而不再一次次在夜里痛苦地醒来,并坐望到天明? 长久以来我想写一本书,但我所构想的一切正受到生活的嘲弄;长久以来我与一些从不存在的女人为伴,现在我明白了:这些假天使肢解了我的生活,毒害了我的心灵,却不能成为这部书中的主人公。我的主人公,命中注定只能来自北京的一条胡同。我们自幼接受的一切造成了我们的现在;我们从不认识的苦难,使我们走到了一起:它在一开始使我们不与生活妥协,现在则互不妥协;它使我们彼此相像,虽然又如此不同。它带来的夜,我们至今仍未走出。它书写着我们,爱我们,威胁着我们——它是暴戾的,我们却像狗一样对它忠实。 于是我把你带在我的生活里(我竟不知这也正是它的要求),如同我们仍住在北京西单那两间低矮而潮湿的老房子里;我在那里同你争吵,但又不得不去爱。我有时以为把你忘了,并为到来的自由欢呼,但你又回来了——那在黑暗中支配我们的一切也变得更邪乎了!你读了那么多女权主义理论,如同你赴美后添置的衣服——你从衣橱里取出一件,试试,扔在地板上又去取另一件:你拥有太多的真理。而我,只读过一本《简·爱》,并且至今仍不清楚那阁楼上的疯女人究竟是谁;她从不露面,黑暗的楼道里却起了火她从不露面,却通过一个个我认识的人,高唱着战歌向生活复仇。 于是我看到控诉暴力的人,其实在渴望着暴力;那些从不正视自己的人也一个个在革命的广场上找到了借口;同样,那些急于改变命运的人,正被他们的命运所捉弄。从当年的红小兵到女权主义者,从“解放全人类”到“中国可以说不”,人们一个个被送往理论的前线,并在那里牺牲,可是我多么希望你不!你也不再是那个走向金水桥头,举起右手向着伟大的领袖的遗像悲壮宣誓的小丫头了,现在你出入于高等学府,说着一口英文,有着我所欣赏的潇洒和知识分子气;但在你的这首诗里,又是谁,仍在攥着那只多年来一直没有松开的小拳头? 而背叛的金色号角奏响,如昆德拉所发现,它甚至就在做爱时随高潮而来的那一阵黑暗里。什么叫忠实,什么叫不忠实,对于这一代人已没有意义;几千年的封闭造成了我们现在的自由,也从来没有一双更高的眼睛在注视着我们,除了街头广告上那些眩目的诱惑;而早年贫穷的伤害,不仅在加速着一种地狱般的贪婪,也使你我的自尊变了形;在同胞们的欲望尚未满足之前,你同他们侈谈什么诗歌,或“人性”?智者早已放弃。而我也渐渐羞于对人们说我是一个诗人,甚至——对我们唯一的孩子。 你在诗中提到了戴安娜。戴安娜的死让我震惊,让我不敢相信,但我想已没有任何人可以同我分担这种震惊。在这里我同一位从巴黎来的艺术家谈到这种震惊,“呵,你爱她?”他笑起来。是呵,他还年轻。他不懂。要目睹命运的威力只有在亲身经历了恐惧之后,要学会爱也只有在认识了苦难之后……这也许仍是我:一个白痴,仍踉跄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混合着狂笑的风雪中,在一个疯狂的世界要求着理解;这也许就是我,心如石铁,坐而不动,震慑于那偶尔从黑暗中向我显露的一切,并从每一种现实的欢笑或争吵中听到一种隔世的悲音——而这些,对你讲又有什么意义?你已不屑于去听。 背叛的号角早已奏响。从什么时候,离,还是不离,这抓住了无数个破裂家庭的问题,在我这里变为去成为还是不去成为?——成为某种人你必须付出代价,甚至你仍在爱的一切,你像牲口一样贪恋的一切……但已别无选择。那长久以来造就我们的一切已照亮了一个寒冬中的额头;而每一次的伤害和震惊,也都在促成着这一步。现在,你迈出去了,虽然那来自黑暗中的力量仍在拉你回去,虽然,一种巨大的荒凉也会时时哽上你的喉头,但你迈出去了——也许我们有一天都会回头,但不是现在。 现在,如人们所说,我们“自由”了。你开着你的旧尼桑,驶向你学习和执教的美丽校园,或者准备着又一个烤肉聚会在仿中产阶级的后花园里,间或来信“过得怎样”?回答当然是“很好”。你准备着你的金色的未来:绿卡,博士论文一辆梦想中的更高档的红色跑车……而我,姑且如此说,在准备着自己的死,一个可以让我去死的死。这是你无从理解,我自己也想象不到的勇气——我为此而生。我到很晚才认识到这一点。我的黑暗中的童年向我涌现,我所敬仰的亡灵一一在这里显形;我的命运升起,闪闪布满了古堡的夜空。我向我的命运致礼,我认可了我的失败。我的全部生活是一个失败。我根本就不配这神圣的婚姻。我不会给一个女人带去她想要的一切。我更对不起孩子和我自己。但也许我将再生——如果我把自己深深埋入这种失败。 起风了!多美呵,德国南部的秋天——只一夜霜寒,山上山下的树木全变了,只有古老的橡树在坚持着……起风了,风也一定从北京的上空吹过;这生命的大气流,也一定会使那座北方的城,浸在海水的蓝色里;起风了,风已深入到记忆的瓦缝里……起风了,是到了“建筑房屋”的时候了,而风,却执意要把你带走,要把一个像动物一样不愿离开的人带走……起风了!我们是在宇宙的无穷里,生命的回流里,我们谁也无法止息这满山秋叶的吹动,我们,我们,把自己交给风…… 悲剧?也许——如果有一种美,一种像冰雪一样震撼人心的力量从中诞生。这是一场已走到尽头的婚姻;这是一场你我必然去经历的死。多少年了,钢琴与电钻的协奏——多少人在做同样的努力,为了怯懦,为了恐惧,为了父母和孩子,也为了一份中国人的面子……八月中,我刚刚从外地出差回到北京,一位朋友就约我到街头夜市,听他谈生活中的变故,谈坚持的悲壮,看他胳膊上的那道刀痕——那是他与妻子吵架时自己砍下的……“中国人,你为什么不离婚?”我想问,嗓音却无比发涩。命运在对人人做着鬼脸,你该去安慰谁? 活,为什么活?爱,为什么爱?是不是因为惟有它在拯救着我们?让我感激我的失败;因为在我的失败中,我开始认识苦难;在我的无可挽回的失败中,我在朝向一种更高的不可动摇的肯定……现在,就算你是你所宣称的“唯物主义者”吧——存在决定意识。但什么是存在这首先是个问题。高大的美式冰箱是一种存在呢还是夜半敲在你屋顶上的雨点?银行中的存款呢还是内心中的某种缺憾?我不再争辩。如果我同你争辩,亲爱的,我们仍是在去精神病院的路上;我们知道伟大的生命在为我们准备着什么,它为我们同时准备了砍头的利斧或挂冠,准备了古老的敌意,疯狂,懊悔,或一只用来拧开煤气开关的绝望的手;它为我们准备了一场永无解脱的苦难循环,但也准备了一个吹号天使,准备了宽恕,感激和自由…… 于是在这困难的日子我一再想起这伟大的诗句:“愿有朝一日我在严酷审察的终结处,欢呼着颂扬着首肯的天使们……”而我是否正接近这个末日?在我的全部生活和磨难中能否响起这一声贯彻生命的欢呼?我又能否在一场预先会失去的爱中获得再生?不,雪已在我写给弗兰达的诗中,如篝火一样升起——我只能把贝亚特丽采还给永生的但丁;我只能回到我的孤独中来;黑暗中的天使尚未把我完全击倒在地,因而他们也不可能出现在我的汉语的上空。我还有更为泥泞、艰巨的路要走。我们的蒙面人尚未为我们最后到来。我的这首诗也写得过早——多少年后,它注定会为另一只手无情地修改。 是到了再见的时候了——平静下来,你仍是我亲爱的人,平静下来,愤怒会化为怜悯,而挽歌也应作为赞美出现。我们有过那么多患难相助的时刻,相亲相依的时刻:俄勒冈烟雨迷蒙的三月,当车刷拨不开浓密、连绵的雨水,我多想在浪迹天涯的无助中握紧你的手;而在五月,当我们一起驶向大海,你和儿子是多么开心呵:蔚蓝的太平洋闪闪透过松林,一会儿豁然开阔地出现在了面前:无限!在那一刻我们的手拉在一起——当一种更伟大的存在对我们讲话,我们重又变成了孩子,比那个跑在我们前面欢呼着冲向海滩的孩子更小……我多想把你留在那一刻!但我们又回来了。大海远去。大海,已不屑拯救我们。 是到了告别的时候了。我曾一再推迟,一再抱着希望,但另一个勇敢的女性已经诞生,勇敢的人们在彻底否认他们的过去——为他们祝福吧,宽恕,理解和和解已不是我能期待的事;每一个人都在追随着他们自己的神,每一个人都将变成另一个人。四十而惑,但我也听出了命运的一些低语,我在辨认着宇宙的伟大法则。我仍将把你带在我的生活里,血液里,或一首献给这个正在逝去的世纪的挽歌里。一如既往,我还随时准备向你的愤怒或欢乐致礼。而我,在我写完这首诗后,冬天就会沿着森林大道和花园小径向我走来,霜雪也会蒙上我的明亮的窗户;大雪封山之前,人们还会纷纷离去。那不勒斯的女儿也将飞回温暖的家乡过冬。而我将在这里留下。我想我已经准备好了:从持续不断的降雪中,从笼罩着山上山下和万物的静寂中,将会静静地升起一支冬日的颂歌…… 1997.10.——1997.11. 写于斯图加特SOLITUDE古堡